“悲剧逼得我非要讲话不可”
半个多世纪以来,谢晋一直是中国电影的一位真正先锋,他在整个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谢晋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外国研究者的权威专访是在2002年12月27日,采访者是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地点上海。白睿文现任职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和流行文化。本报获得白睿文先生的许可,首次在中国公开发表他与谢晋导演的部分访谈内容,小标题为编者添加。
“要为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
白睿文:您在1964年拍摄了《舞台姐妹》(blog)。这部电影的命运很乖舛,将近十年之后才获准上映。您拍摄《舞台姐妹》的时候,不曾想过会遭受这么大的批评?
谢晋:根本不会想到,那时谁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没想到会遭到这种命运。他受到严厉的批斗,邓小平也是。邓小平被打倒了几次,送到江西劳改。他又复出之后,问我们的国家怎么会搞成这样?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倡议了很多政策上的改革。他跟所有人一样都有同样的疑问——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这问题看得太小了,整个国家都陷入混乱,连国家元首都被打倒。
我为什么拍悲剧?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说话不可。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们说话。要为这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所以像《牧马人》、《芙蓉镇》都是在极大的激情之下拍的。如今很多人都在谈歌舞片、数码片,认为那是观众唯一关心的。其实相反,只有对社会生活真诚的感情和切实的反省才能打动观众的心弦。《天云山传奇》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文革期间我们有很多冤案。胡耀邦做总书记时把几千万人的冤案都平反了。所以这部电影在这个时机出来,获得很大的共鸣及世界的注目。《芙蓉镇》也是,中国的问题不看这部电影你不会了解。
《芙蓉镇》到日本上映时,日本人说:“谢导演,原来是这么可怕的灾难,这么小的镇子也发生这么大的悲剧,你们真是苦啊!”经由我的电影,人们更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是不可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的,因为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美国人怎么会过这种生活呢?所以必须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才能了解我们的电影。
“会有真正反省文革的杰作”
白睿文:上世纪70年代文革期间,电影导演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而无法拍摄电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时间您作为一个电影人,仍持续您的电影梦——或该说是噩梦?
谢晋:在这样的年代拍摄电影,是什么样的景况?文革的时候我拍过电影,拍过样板戏。当时虽然还没复职,但是什么都打倒了、都没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电影导演就被指派拍样板戏。这些戏都是当时政治气氛的产物;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场噩梦。不光是一场噩梦,我父亲吃安眠药自杀、母亲跳楼自杀,都是我去把他们抱上来的。当时我还关在厂里不许出来。一开始我很自责,后来也想通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那不只是针对着我,即使那些创建我们国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计以后会有很多的作品从这场悲剧里出来,会有真正反省文革的杰作。这是人性的毁灭,发生在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提到“文革”总会称它“史无前例”。我们应当记得这个词,“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过。
中国以后一定会出现非常重要的作品。我想,研究一个国家的电影,尤其是重要的电影,要了解很多那个国家的历史背景。越战结束后有些电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也不会有这些电影创作出来。后来我几部主要的电影也一样,像《天云山传奇》。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作者: emer,
转载或复制请以 超链接形式 并注明出处 EMLOG。
原文地址:《谢晋生前专访:愿我的电影给中国人希望(图)》 发布于2024-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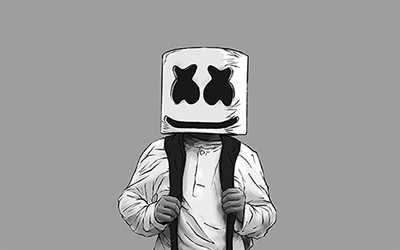



最新评论
回复了emer:二级回复测试
打卡成功,现在时间:20点6分记得每天坚...
对方不想跟你说话并向你丢了一朵小黄花[a...
打卡成功,现在时间:12点0分记得每天坚...
啊
11啊
测试
回复了emer:测试
测试
这是系统生成的演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