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松
近日,曾被称为“青春残酷”一代艺术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尹朝阳,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由朱朱为其策划的个展《正面》,展示了2007 年以来创作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它们充分表现了艺术家对在欲望与虚无中扭曲变形的种种人生处境的敏锐触摸与冷静描述。
初次碰见尹朝阳,还是在2004 年春天,上海的多伦路上。当时他留给我的印象,是结实、京腔、话少,沉默时让人觉得有点傲,说话的时候,会自然地略微眯起眼睛,声音低沉,节奏平缓。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展览开幕后的第二天,陪他去上师大给向京和瞿广慈的学生做讲座。面对学生们,他说他不习惯坐在讲台上说话,因为展览的缘故站着讲又很累,于是就选择坐在椅子背上,双脚踏着椅子座。然后他就从自己早年推着三轮车,把画运到一个博览会场外摆地摊的事讲起,将自己的绘画以及生活的经历与变化慢慢道来,偶尔还会意外来点冷幽默,让那群学生笑个半天。他每讲一段话,似乎都要经过深呼吸。
那个展览是在多伦现代美术馆举行的,名为“乌托邦& 青春物语”,听起来有些时髦得古怪,不过看过那些场面宏大、感情独特的作品,就觉得倒也切合主题。当时的评论里,有人喜欢拿宏大叙事套尹朝阳的作品。其实,他所描绘的,完全是站在个人角度上想象出的情境世界,而不是历史的、社会语境下的叙事冲动。朱朱从“双重自我”的角度切入当时的《乌托邦》系列大体是准确的,一个自我在想象中“将个人的青春加入到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大合唱之中……还想在其中扮演起英雄与领袖的角色”;另一个则“冷眼旁观这一切,他深知那种革命激情所具有的虚幻、谬误及其意识形态中令人反感的一面”……但是现在看来,那第一个自我的心境,实际上倒更像是一个成长中的男青年,在异常孤独的状态中,对那被神化了的领袖人物所进行的角色体验式的介入—就像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穿着父亲的军装站在镜子前那样—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孤独与伟人的孤独、自我的激情与伟人的激情、青春的幻想与被神化的理想之间的奇特共鸣。说到底,无论是置身其内还是冷眼旁观,那“双重自我”都处在疏离于现实大背景的异乎寻常的孤独情境里,他听得到那些所谓的主义与合唱,但是从内心讲几乎等同于置身事外。所有的场景画面似乎都是开放着的,但实际上又都是封闭的,是只对“双重自我”开放的完全个人化的想象视界。
时隔6 年,在上海美术馆看到尹朝阳新的个展“正面”,之前的那些印象仿佛一瞬间就被翻到了背面。这一次,没有看到任何大场面,有的只是人,个体的人,或者少数的几个人。主导画面的,仍旧是红色。但这一次的红色似乎只与血气有关。尽管红色在整个画面中的比重并不大,但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无所不在。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正面》、《赵棒》、《老蒋》等系列作品。仔细看这些画作,就会发现,那些人既像处在生命力爆发的失控状态中,又像七窍流着血缓慢坠入玻璃水池里,暴力的实施者与受害者仿佛同时存在,狂妄、卑微、迷茫、骚动等诸多力量混杂在一起,裹胁着他们,持续扭曲着他们;有的人像是正在经历从人变成某种猛兽的过程,唇边已长出锋利的白牙,而有的人则仿佛沉湎于烂醉的亢奋而又疲惫不堪的幻觉中不能自拔。如果说,从上述这些以人物为主的系列作品中仍旧不难发现6 年前同类作品中的思考线索的话,那么在《黑色背景》、《红色背景》、《灵与肉》等系列中,尹朝阳所展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视界:他的那些极富表现主义特色的笔触似乎穿透了日常状态下的人物的外壳,进入到非常状态下的人体内部,进入灵魂的内部,感觉的内部,紧紧地缠绕着那些交织抽动着的神经束,使得身体的变化与灵魂的变化不断纠结在一起,从而展现出一幅幅灵肉交融而又剧烈冲突的、界限难明的人物图景。或许我们可以仔细揣摩一番这些仿佛剥了皮的完全模糊了的人物形象原型来自何处,他们显然是有着特定的出处的,但是查明出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其实是体会到画家所要传达的曾经重要的某些典型形象的消解过程。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如果不具其名,有谁还能认出他们?可是谁又能说他们如今的形象比过去的形象更不真实呢?同时被消解的,注定还包括那些被人们虚构上去的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些作品从形式上说,很像是画在墙壁上,而不是画布上,甚至会让人想到涂鸦,但显然它们更接近于岩穴壁画的质感,只是更为复杂而已。
时间改变了一切,同时将一切抛掷向遥远的地方,变得比任何传说还要难以辨析和理解,那么究竟把什么留下了呢?或许就是一个极其诡异、动荡不安的剧变中的世界吧。
实际上整个展览中最令人惊讶不已的,还是《大洪水》、《四季岛》这样的作品。颇耐人寻味的是,两幅创作时间相差两年、内容完全不同的作品中,竟然有个非常相似的人物形象出现—一个巨乳肥妇半蜷缩着身体,右手撑地,左手握着个苹果,正在咬着,只有表情不大一样。在《大洪水》中她是游离的,几乎躲在画面边缘,不那么引人注目,在她身旁的则是神态悠闲坦然的两个肥妇,这三个肥女形象虽然只占到整个画面的六分之一上下,却与其余充斥着灾难气氛的部分构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在《四季岛》里,那个毫无羞耻意识的肥婆则占据了主要位置。这两个吃苹果的女人除了让人联想到“原罪”之外,还有什么呢?或许就是“欲望的洪水”。在画家眼中,那两个体态丑陋的肥妇或许正是持续膨胀的欲望的象征;可能总有一天,人类会因为对欲望的纵容与失控而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以至于重新退回到史前大洪水时代的生存状态里,甚至可能回到人类祖先的身边—《大洪水》左上角那个像是类人猿的形体,难道不就是一个暗示么?
这里没有美,没有悲剧,也没残酷命运的凄惨,当麻木与堕落、欲望与贪婪、绝望与虚无的气息交织在那样臃肿异常的女体周围时,你或许会冒冷汗,然后哑然失笑,因为你发现这最后上演的,只是无可救药、毫无意义的尴尬闹剧。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作者: emer,
转载或复制请以 超链接形式 并注明出处 EMLOG。
原文地址:《尹朝阳:在欲望中扭曲的正面(图)》 发布于2024-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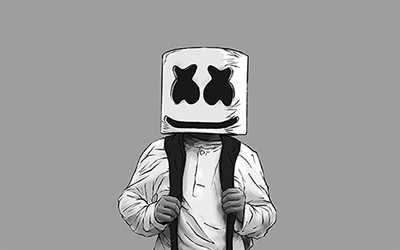







评论